在深圳26年的“文化之旅” - 杨宏海
摘自:深圳商报
“1985年,我从内地高校调进深圳,转眼间已过去26年。在这26年中,我一直与这座城市的‘文化’结缘。”昨日上午,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、文化学者杨宏海在接受深圳商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如是说。
杨宏海的新著《我与深圳文化: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文化史》,近日由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出版。该书系统反映了杨宏海近30年的文化历程与学术成就,包括他在深圳特区文化各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成果,如对特区文化的理论构建,记录“打工文学”、“阳光写作”等深圳文化名片的诞生与发展;同时还以较大篇幅承载了这位从客乡沃土中走出去的学者,在文化研究中与客家文化血肉相连的情感,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一系列创新实绩。
书写“我”与城市文化的成长史
《我与深圳文化》分为上下两卷,涵盖了《文化深圳》、《都市百态》、《打工文学》、《阳光写作》、《创意无限》、《客邑人文》、《月照围楼》、《编外钩沉》、《纪事珠链》等9章的内容,共计130万字。该书还有一个副标题——《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文化史》。
为何书名中既体现了“我”,又突出了“一个人”?对此,杨宏海坦言,这并不是一种“自诩”。“我意识到,在这座曾被人称为‘文化沙漠’的城市里,‘文化深圳’是每一位城市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。事实上,千千万万的‘我’正在成为文化建设的实践者,正是这千千万万的‘我’与这座城市一起成长,共同创造着一种崭新的文化,谱写着我们共同的‘城市文化史’。”杨宏海告诉深圳商报记者,他之所以取这个书名,是想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其中,以一个历史亲历者与见证人的微薄之力,把参与对文化主体的建构过程叙述出来。
“这种叙述,其实是一种多角度的‘抓拍’,通过专文、自叙、补白、链接、背景介绍、图片说明等多种方式,叙述我与城市的文化史。而且,这是我所喜欢的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叙事,是包括‘我’在内的普通人的历史,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同样应该具有研究价值。在这种理念的前提下,我采用了一种多重互证的写作尝试。”杨宏海说,读者透过这本书,可以看到文化积淀相对薄弱而文化创造又快速发展的深圳,怎样一步一步构建自己的“文化大厦”。
对深圳文化研究涉猎甚广
在过去26年中,杨宏海与深圳的“文化”这样结缘:先在深圳市文化局工作8年,继而创办并主持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8年,之后又调任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10年。
“这些年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关怀和培养下,我几乎参与了深圳文化开拓、建设与发展的全过程,参与了影响深圳文化发展的绝大部分重要文化实践,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收获了耕耘的成果。”杨宏海告诉记者,作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工作者,他欣喜地发现,深圳文化已“从曙光初露到朝阳出海,景象蔚为壮观”。
早在1997年,杨宏海就出版专著《文化深圳》,记录深圳特区创业时期的文化追求和梦想。而如今付梓的《我与深圳文化》,则囊括了他对深圳特区文化的探索思考。
阅读《我与深圳文化》,会发现杨宏海对于深圳文化的研究涉猎甚广,并且常有创新之举。比如他以政府文化工作者的姿态,开创特区文化研究中心,融政府与专家视野为一体;他首提深圳“现代文化名城”定位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城市方略,并参与首倡“深圳读书月”、“市民文化大讲堂”等市民文化公众活动;他率先对“华侨城”旅游文化进行调研,撰文总结经验;他率先推动深圳“非物质”文化遗产保护;他率先扛起“打工文学”、“阳光写作”等文学新类别旗帜;他又以学者的视野,悉心钻研客家文化与深圳“新移民都市文化”;他还亲手主创舞台剧《月照围楼》……如今回首过去,杨宏海说:“不得不说是命运的选择,是冥冥中的一股力量,引领着我在文化之旅中坚持跋涉、一往无前。”
持久关注“打工文学”与客家文化
杨宏海对特区文化的坚守,比较突出地表现在对“打工文学”与“客家文化”的持久关注与研究上,这也是他文化研究成果中不可或缺的两大板块。
经过近30年的发展,打工文学已经成为深圳的“文化创举”之一,在全国文学界中也受到关注。而最早提出“打工文学”概念的,正是杨宏海。他不仅切实关注外来劳务工的精神生活,还为实现外来工的文化权利鼓掌欢呼。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,“打工文学”成为深圳文化风景中的亮丽品牌:举办了6届“全国打工文学论坛”;编辑出版《打工世界:青春的涌动》、《打工文学纵横谈》、《打工文学备忘录》、《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》等相关著作;为提升“打工作家”文学修养而举办多种文学培训班;组织体制外作家到海外考察,拓宽其视野等等。
身为客家人,杨宏海对客家文化研究也自成一体。他从“粤东客”的独有民俗着手,对深圳的民间歌谣、客家民居所蕴含的移民文化特征进行了全新的文化阐释;他认为,应当让中华精神的支脉——客家精神赓续绵延,薪火相传。对客家文化个案,如“黄遵宪与民俗学”、“丘逢甲的军事思想”、张资平、李金发等小说家与诗人,他更是悉心研究,编纂《深圳民间歌谣》、《客家诗文》、《客家艺韵》等著作。杨宏海还在深圳创办“客家文化节”,并融入每年的“创意12月”,让传统客家文化刮起创意旋风,深得各界好评。因其对客家文化精深钻研及其实绩,作为名家工作室之一的“杨宏海客家文化与艺术工作室”已成立运转近两年。
谈及这些扎实的成果,杨宏海说:“在‘文化深圳’的征途中,我紧跟时代的脚步,一刻也未曾停歇。”
相关链接
名家评价
《我与深圳文化》
黄树森(广东省政府参事、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名誉主席、编审):
杨宏海与他的专著《我与深圳文化》,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“本土文化研究”的范本。此之谓“本土”,与其说是一个实存客体或一种“民粹主义”立场,不如说他首先意味着一种知识的“态度”,是知识分子(或某类特定的知识分子)与现实发生关联的方式。基于“本土”态度,我们提倡首先对自己的问题作扎扎实实的研究,立足其上提炼、形成有理有据、得体得法的研究体系与方法。而我观宏海以及宏海此专著,恰在此宏大命题上,率开先河。
在深圳“本土”理论饥渴、文化自觉初步觉醒的当下,《我与深圳文化》此部“极接地气”的佳作,更似“乳燕初声”,带给这个城市满心喜悦。
胡经之(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文艺美学家):
《我与深圳文化》从“单个人”的视角透视深圳30年文化的历史变迁,将个体文化实践与一座城市30年的文化发展相关联,以一个人学术研究、艺术创作的历程,见证与展示这座城市30年的文化发展轨迹,确为盘点与回眸深圳文化30年的一个新颖视角。
“一个人眼中的深圳文化”,看似简单,实则不然。首先,此“人”必须要具有“窥一斑而知全豹”的“眼”;其二,此“人”与“深圳文化”,需得血脉相连。宏海调入深圳时间早,属于特区文化“场”的主要开拓者。谈及深圳30年文化史上许多标志性文化事件,都绕不开杨宏海,如“特区文化”、“打工文学”、“现代文化名城”、“文化产业”、“深圳精神”、“深圳文化大讨论”、“深圳读书月”、“市民文化大讲堂”、“新客家文化”、“阳光写作”等等。所以,杨宏海的《我与深圳文化》,从框架与粗线条上正是深圳文化这30年来的律动与变迁的写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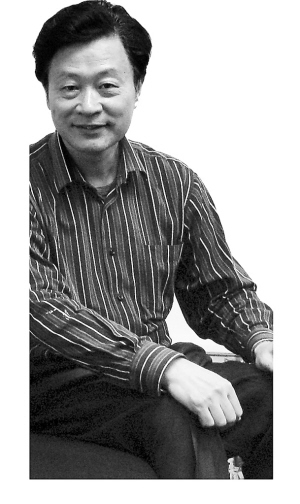
身为客家人,杨宏海对客家文化研究自成一体。( 钟华生 摄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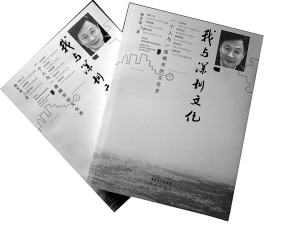
▲杨宏海的新著《我与深圳文化: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文化史》(钟华生 摄)
2011年6月13日
|